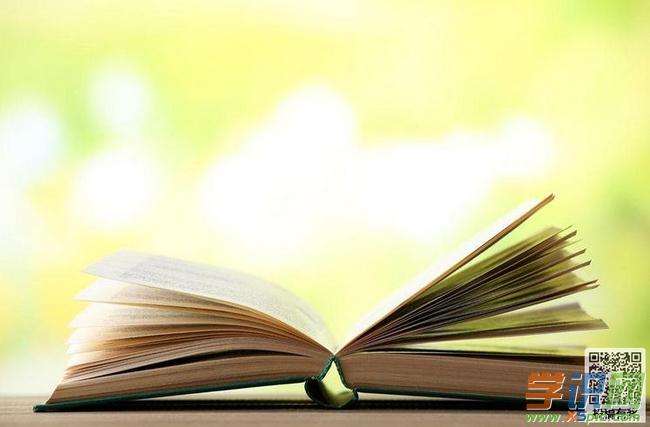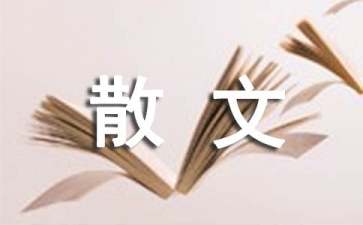小说节选:接生婆的故事
接生婆

村里有一個接生婆,叫春娭毑。
一双小脚,如一对粽子。头上绾着一个结,常年穿着一身青色衣裳,拄着一根拐杖。
她家住在清代的老房子里,祖上有一个在外做县太爷的,修了四进大屋,“土改”时,春娭毑家属于贫农,便分在第四进原属于地主放杂物的房子,她的丈夫瑞升爷,仍旧蓄着白色的胡须,家神堂的祖宗牌位都拆掉了,换上了一幅毛主席画像,瑞升爷以为是孔夫子,天天要鞠躬。
平常的日子,当太阳从天井内照进堂屋里,瑞升爷坐在太师椅上,照例晒太阳,一只老猫偎在他的脚边。春娭毑则戴上老花眼镜,找出一堆花花绿绿的碎布片,她要把这些东西糊成垫底,糨糊早就用小锅熬好,纸样也剪好,一层层地涂抹,再压紧。日子就这么恒常地流逝,待日头快移到家神神龛前的香炉上时,春娭毑停止了糊垫底,她要去做午饭了。
她的日子偶尔被外来接她的人打扰,人家很急,轿子停在外面,她有时正在煮饭,马上关了火,也顾不得给瑞升爷做饭,人命关天。
她洗一下手,赶紧从大柜里找出那个蓝色的包袱,把一把剪刀塞进去,还有一条土布织的毛巾,一个洗手的铜盆子,便麻利地把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下后,把头发梳理几下,似乎已经油光泛亮了。她坐进轿子,一前一后的轿夫便闪闪悠悠,从家神堂的幽暗里闪进晒坪里的阳光中。
生崽的人家,在邻近的上庄。轿夫便要过塘坎,他们的影子就映进碧蓝的水里。塘坝上那棵杨树上,有几只鸟忽地腾空,似乎目送着春娭毑的出行。
迈过几条田埂,在一片油菜田边穿过,一些蜜蜂嗡嗡地追赶了一段。还要过小溪流,几块鹅卵石供人跳着过河。再就是爬山了,山路七弯八拐,把轿里的春娭毑一颠一颠的,好在她已习惯了这种山路的爬行。即使夜里,打着火把,树上的猫头鹰一阵阵地哀鸣,溪水里的青蛙,也是咕咕地噪鸣,她也在这种大自然的天籁声中,假寐一会儿,等下接生时更有精神。
一般接春娭毑去接生的人家,有慕其大名的一些民国时期生的父亲,也有70年代出生的儿子,再就是遇上几天几夜发动了,生不出来的人家。他们不请赤脚医生,认为春娭毑她经历得多有办法,甚至有神助。春娭毑也对得起她几十年接生的这双手,她不记得究竟是接过多少个孩子,但只要说起某某的姓名,她都会记得这孩子的出生日期,生辰八字,何种属相性别。
上庄邓姓家的媳妇,已经发动了三天三夜,就是生不下孩子,媳妇是头胎,一个圆滚滚的肚子,如一面大鼓。一家子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还未出轿门,就能听见那媳妇儿在床上不断地呻吟。
相关阅读
-

小说故事:牛粪也有着独特的清香
官里传出消息,皇上纳妃,当朝官员如有待嫁女儿,可以将画像上呈甄选。 李知府很激动,他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待字闺中。 当然得先找一名画师。 应征者络绎不绝,经层层筛选,入
-

生活随笔:心地善良,心怀悲悯,一生定能行好运
清晨的校园里,清风习习,鸟鸣啾啾。 一如往常,在学校操场边的一排香樟树下,我胡打了一通自创的“五禽戏”,拉伸后,准备再做一百个俯卧撑。刚趴下来没做几个,突感有东西掉
-

旧故事:父辈们
台湾的十六弟书仁,清明节要回老家上坟,我去郑州飞机场接他。 十六弟是九叔父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特别像二奶奶。机场出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九叔父去台湾前是国民党洛阳
-

生活随笔:回忆,过去的甜味儿
北方人嗜酸,南方人爱甜,肉羹里都放糖。汪曾祺老先生说:“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肉包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饭菜里都放糖,虽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