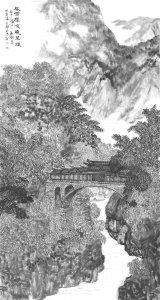生活笔记:我在俄罗斯当倒爷的日子
我在俄罗斯当倒爷
张多奎

过去的老北京,管倒弄衣服、手表之类的小商小贩叫倒爷。国门打开以后,边城人管倒爷也叫倒包的。最初的倒爷,不过是从乡下收来几筐鸡蛋或者鸭蛋什么的,然后小心翼翼地搬回城里换粮票,或是打南方论斤称来电子手表,用军帽装了到各地大城市里去兜售。总之,他们是缺什么就倒什么,什么紧俏就倒什么。倒爷是那种善于抓住商机的人,他们以低价买进,再以高出原价好多倍的价格卖出去牟取暴利。
早年,说谁谁是个倒爷,这话里是多少带有些贬义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倒爷是涉嫌投机倒把、碰触法律红线的人。倒爷在国内遭受打击之后,很快就把目光转向了俄罗斯,当起了国际倒爷。改革开放初期那几年,就有好些人从绥芬河口岸出境,往俄罗斯那边倒包。列车开入俄罗斯境内,每到一站,倒爷们就拎着皮夹克或羽绒服之类的轻工产品蜂拥而下,而此刻,站台上早就挤满了等待抢购的俄罗斯人。国际倒爷在境外赚得盆满钵满,让那些循规蹈矩的内地人好生羡慕和眼热。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辽宁海城西柳服装市场批发“阿里达斯”运动服,然后把货倒卖到边城绥芬河。有一次,我在去西柳进货的火车上,有缘认识了一位来自同江下海经商的冯老师。冯老师有护照,他把从西柳进的货打成包,坐国际列车带往境外,到那边卖给俄罗斯人。后来,我通过冯老师帮忙,给我和我妻子、我弟弟,还有我外甥,每人办了一本护照。去俄罗斯倒包,一点儿俄语不会是行不通的。当时,绥芬河地摊上到处有卖《俄语自学入门》的小册子,我就买了一本在家自学,学一些日常交流的俄语单词和对话用的短句子。我对照上面标注的汉语发音反复念,也不管标准不标准,更不知道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俄语,俄罗斯人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出境后,我兜里也揣着书,到大街上直接找俄罗斯人练习对话。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边现学现卖,一边观察俄罗斯人都喜欢抓什么样的中国货。
带我和我弟弟出国的是一位叫赵红的中年妇女。她会说俄语。那次,我们是中国时间下午一点乘坐俄方国际列车出境的。带货登上国际列车之后,我一下子就蒙了。整节车厢里,我听到的是几乎完全听不懂的俄语,还要忍受俄罗斯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狐臭味儿。实在受不了了,我只能去火车的车厢连接处透透气。有俄罗斯人躲在车厢连接处抽烟,我又受不了烟味儿。俄罗斯火车在运行途中是严禁打开车窗的,车厢里闷得像个蒸笼。强忍了两个小时,列车终于开进了俄罗斯格城。验完关,赵红打车带我和我弟弟去她经常住宿的一户俄罗斯人家。洋房东盛情地端出来酸黄瓜和奶酪招待我们。他们身上更浓的气味儿熏得我和弟弟没有食欲,勉强吃几口就躺下休息了。第二天,来接货的朝鲜族人把我们的羽绒服全部买走了,带往俄罗斯内地,转手他就能大赚一把。货顺利出手,我和弟弟就乘坐中方的国际列车回国了。成功当了一把国际倒爷,让我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心里自然是有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在回国的列车上,我还认识了几位来自望奎的老乡,我们约好了下次一起出国,彼此间也好有个照应。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回忆,过去的甜味儿
北方人嗜酸,南方人爱甜,肉羹里都放糖。汪曾祺老先生说:“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肉包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饭菜里都放糖,虽然味
-

旧故事:父辈们
台湾的十六弟书仁,清明节要回老家上坟,我去郑州飞机场接他。 十六弟是九叔父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特别像二奶奶。机场出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九叔父去台湾前是国民党洛阳
-

生活随笔:心地善良,心怀悲悯,一生定能行好运
清晨的校园里,清风习习,鸟鸣啾啾。 一如往常,在学校操场边的一排香樟树下,我胡打了一通自创的“五禽戏”,拉伸后,准备再做一百个俯卧撑。刚趴下来没做几个,突感有东西掉
-

小说故事:牛粪也有着独特的清香
官里传出消息,皇上纳妃,当朝官员如有待嫁女儿,可以将画像上呈甄选。 李知府很激动,他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待字闺中。 当然得先找一名画师。 应征者络绎不绝,经层层筛选,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