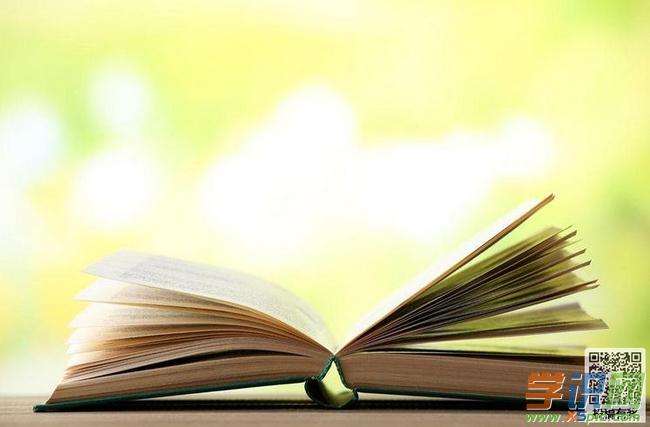散文小辑:诺维萨德的气温(2)
冬天的颜色
多瑙河的拐弯处就是彼德罗瓦拉丁要塞,它是古城诺维萨德的蜡黄的名片。踩着坡度上砂砾往上走,寒风拼死拼活,直往衣领口里钻。是你觉得冷了,还是我觉得冷了?野草缩在泥土里,树木已有几批叶子安顿到土地里了。再踏一路石头台阶,穿过一处20米长的隧道,却是隐约可见的门户,悬挂着金黄的藤蔓。物竞天择吧,应该是近代防御热兵器的隐秘的地道人口。终于感觉到一股热流在身上回旋。
上,继续往上走,到了突进多瑙河的尖角处,好像驶进波浪里的船头。
尖角开阔处是一个小广场,红色的地板砖铺到了黑色的栅栏边,又往斜坡和台阶里延伸。
寒风的攻势猛烈起来了,小广场上仅有的一棵大树,放弃了全部的叶子。挺在大树前面的钟楼,被刮得时针短、分针长,依然指引着多瑙河上航行的船只,从不枯萎,从不落叶,从不改变颜色。
这座钟楼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不可能见证两千个形形色色的冬天。如古罗马帝国的剑,如何刺杀了多瑙河的浪花,洒下雪白的血;又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奥地利与土耳其的霸王之争,如何祸及多瑙河的鳟鱼,产不了春天的卵。它祈祷现代的好日子,却在冬夜已尽、春寒悄然的覆盖里,被现代科技精准制导的炮弹震醒了。
连接要塞与古城的铁桥,与许许多多的无辜一起,被摧毁在多瑙河的烟波里,留下几截仇恨的桥墩。20世纪末的彼德罗瓦拉丁要塞,从40米高的火山岩石里探出头来,不停地搓着双手,连杀一条鳟鱼的力气都没有。这是颜色之争吗?不,冬天已经突破了季节的界线,这块土地已经改变颜色。
一只漂亮可人的狗,黑黄相间的毛,一直跟着、粘着王菁。她是我们一行里最有色彩的朋友。
我拿她的手机,给她与它的友好拍了好几个画面。背景是多瑙河新修的大桥,横贯东西。
下午的诺维萨德突然暖和起来。
“墨迹天气”还管用,它告诉我,诺维萨德市中心的自由广场是舒畅的16%。
我在广场上转一圈儿,却是满地杂乱,一片随意,肯定是一场狂欢刚刚过去。
高耸的铁架子,还挂着聚光灯;两只白色的大绵羊,还绕着一串彩灯;一座座紧挨着的胶塑小房子,还等待着夜晚的到来。
狂欢的主题是什么呢?也许什么主题都没有,就是为了跳一曲塞族的舞蹈,弹奏一支多瑙河的曲子,买两盒奶酪,见心爱的姑娘。
或者,純粹是为了花掉冬天的时间。
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座铜像,也和人们一起狂欢。他是斯韦托扎尔米来迪克,曾于1861年和1867年,两度当选诺维萨德市的市长。
市政厅在广场一侧。这是一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四层建筑,原是诺维萨德法院。他从没在这里上过班,却在这里受到奥匈帝国当局的叛国罪审判。1876年的冬天,一辆囚车从这里驶出,将斯韦托扎尔米来迪克押进了监狱。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回忆,过去的甜味儿
北方人嗜酸,南方人爱甜,肉羹里都放糖。汪曾祺老先生说:“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肉包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饭菜里都放糖,虽然味
-

旧故事:父辈们
台湾的十六弟书仁,清明节要回老家上坟,我去郑州飞机场接他。 十六弟是九叔父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特别像二奶奶。机场出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九叔父去台湾前是国民党洛阳
-

小说故事:牛粪也有着独特的清香
官里传出消息,皇上纳妃,当朝官员如有待嫁女儿,可以将画像上呈甄选。 李知府很激动,他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待字闺中。 当然得先找一名画师。 应征者络绎不绝,经层层筛选,入
-

生活随笔:心地善良,心怀悲悯,一生定能行好运
清晨的校园里,清风习习,鸟鸣啾啾。 一如往常,在学校操场边的一排香樟树下,我胡打了一通自创的“五禽戏”,拉伸后,准备再做一百个俯卧撑。刚趴下来没做几个,突感有东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