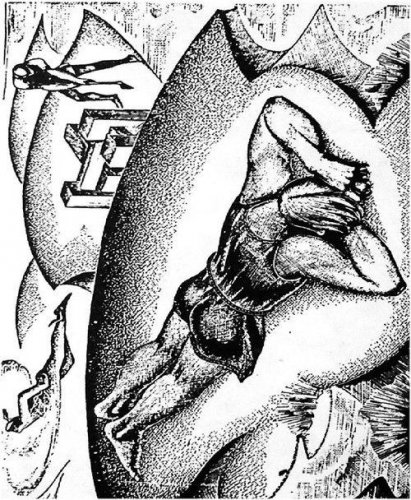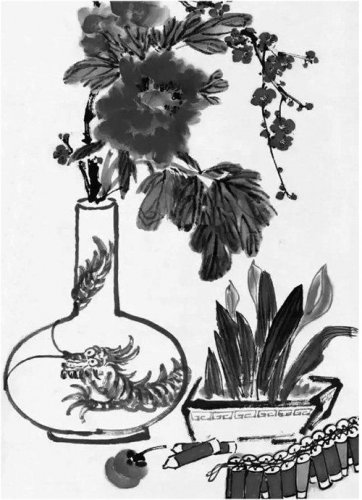生活随笔:我跪着摘棉花的母亲(2)
“跪”着的母亲
母亲死得突然,死得令任何知道她的人揪心落泪!那年,我已经是单位乡镇机构网点的小领导。那一天早上,我到村头堂哥早点店端米粉给母亲吃,嫂子说婶娘喜欢吃豆饼汤,你三姐已经端了。但是我还是端了一碗豆饼汤去老屋。母亲似乎很平静,说今天真好,你们姐弟二人都带了吃的来。我说今天要参加邻镇一个银行新网点开业。母亲说那就去吧!母亲的话其实另有深意,只是虽有疑惑的我没有深想。晚上我刚从村头下车,一个堂哥的喊声如晴天霹雳,我醒悟到今天反常平静的母亲出事了!我跌跌撞撞地向老屋奔去,进村的一路都有妇女在叹惋:“可惜了青山婶,苦命的好人呐!”“她的宝贝儿子回来了,这下有的哭啊!”……但是,我还没有哭。母亲已经被堂哥们嫂子们平放在我出生的那张旧木床上了,她选择了用一根了断苦难的绳索撒手人寰。她的手还是温暖的,我抚闭她含泪的双眼时自己也涕泗滂沱了——她选在我回家之前行动,不知经过了多么残酷的生离死别的权衡!
痛定思痛的时候,我的母亲,这个叫“青山”的、聪慧的、坚强的女人,她艰辛的后半生,在我脑海里放起了幻灯片——从姐姐们寻亲的信件上,已经上班了的我才隐隐约约知道,她们的生父远在安徽。从她们闪闪烁烁的言语里,她们对那个父亲颇有微词,说他是“右派”,多年后才平反,不仅领退休金,而且还有自己的房子,可是没有管顾她们。
母亲曾经是兰州铁路局的职工家属,她带着三个“拖油瓶”到湖北的时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整个社会才开始慢慢复苏。只是让村里人们不解也钦佩的是以她如此弱不禁风的身体、经历婚姻离异的窘况、跨省份的奔波和一个几乎赤贫的老鳏夫重组家庭的现实,完全无能力背负这沉重的“包袱”,她居然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责任担当。这是一种多么坚忍的心性。
我的父亲比她大好几岁,家庭在村里是有名的贫困,虽然耿直、善良,做农活是把好手,却是个脾气暴躁、出了名的“老齁巴”——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不过,多年后一个远房的姑姑讲给我:“你爸爸年轻时脾气好坏噢,说不对就动手!还是青山姐来了后才变好的。”我深信,因为父亲抚育我的那份温情说明了一切。父亲去世前后,朝夕相处的母亲也被传染了这无法根治的老毛病,无疑雪上加霜。
有一年,二姐的年龄好不容易对上了一个合适的招工机会,却因为农村户口而告吹。母亲很多年后才告诉我这事:舅公送她们来的时候兄妹俩只是在流泪,被询问是上农业粮还是商品粮户口时,根本没有作出任何选择,只感觉农村多少还能分点口粮,不至于饿死人。
三个姐姐中的两个,特别是大姐成年后在农村苦干多年,用微薄的工分艰难地摘掉了家里“超支户”的帽子。可紧接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时间里,她们三个的连续出嫁——这也在村里是特例,再一次让这个家一贫如洗。我在单位的账簿上看到从1962 年起,父亲名字的贷款从两三元到一二十元有数十笔,还清几百元的,记满了一整张账页,直到我工作七八年了才还清。
相关阅读
-

小说故事:牛粪也有着独特的清香
官里传出消息,皇上纳妃,当朝官员如有待嫁女儿,可以将画像上呈甄选。 李知府很激动,他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待字闺中。 当然得先找一名画师。 应征者络绎不绝,经层层筛选,入
-

生活随笔:心地善良,心怀悲悯,一生定能行好运
清晨的校园里,清风习习,鸟鸣啾啾。 一如往常,在学校操场边的一排香樟树下,我胡打了一通自创的“五禽戏”,拉伸后,准备再做一百个俯卧撑。刚趴下来没做几个,突感有东西掉
-

生活随笔:回忆,过去的甜味儿
北方人嗜酸,南方人爱甜,肉羹里都放糖。汪曾祺老先生说:“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肉包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饭菜里都放糖,虽然味
-

旧故事:父辈们
台湾的十六弟书仁,清明节要回老家上坟,我去郑州飞机场接他。 十六弟是九叔父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特别像二奶奶。机场出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九叔父去台湾前是国民党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