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新年到了
故乡的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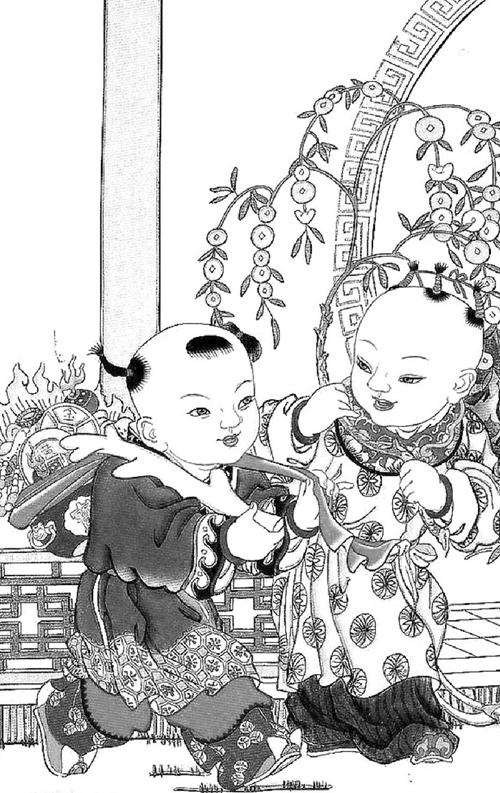
在雪花飘舞里,新年又到了!
腊月二十三四,家家户户蒸馍,不管日子穷富总要蒸上几锅白面馍。大人蒸馍的时候,小孩子不得乱讲话,比如:“蒸完了吗?还有吗?”这一类的话不吉利,说了要挨训的。
枣山一定要蒸。大的、小的,单层的、双层的,还要蒸带枣的小花馍,小鸟、兔子、小猪等,象征着来年的丰收景象。蒸完了几锅白面馍,再蒸些黑面皮的干菜角子。那时候,白面很少,过年蒸的馍不够吃。初一,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团圆饭,吃白面馍。初二起,母亲就再也舍不得吃白馍了,就吃黑面皮的干菜角子。她总说自己爱吃这个,但我们心里都明白,她是怕白面馍不够年关招待客人吃的。那时的黑面是高粱、红薯干、玉米加在一起磨制的,黑而粗糙,吃到嘴里又干又涩。蒸黑面角子可不容易。擀面皮的时候得小心翼翼,稍一用力就裂开了。包馅时,面皮要放在手心里,搁上馅儿,两手捧着,十指稍曲,用力一捂,捏紧边沿,放在锅里。只有蒸熟了才结实些,否则,一不小心,就是一盘散沙。
还有一种用白面与白玉米粉掺和到一起蒸的“白馍”。乍一看像白馍,嚼起来却还是玉米馍的味道,不细腻、口感差。因为白面不足,又不想失体面,在那些年月里,村里就种了一种白玉米。这种馍,不是真正用来招待客人的,而是埋在盛白馍的笊篱下边,当填充物的,显得主人热情、大方,但彼此又心照不宣。这种无奈,现在想起来好滑稽,又禁不住泛起一丝苦涩。
腊月二十六,父亲从城里放假回来过年啦!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把屋里屋外扫了个遍,把桌椅板凳捯饬得整整齐齐。父亲会做麻糖,先把白面、芝麻分别炒熟备用,再把麻糖坨轧砸碎,放进锅里加热融化,倒入芝麻熟面,快速翻动和成面团,趁热擀成薄片,切块拧成麻花,整个过程熟练利落。母亲打下手,我们姐弟几个早已沉浸在了麻糖的香甜里……父亲从城里买回来许多年货,最显眼的莫过于猪肥膘,白花花一大盆,洗净切块放进锅里小火熬。待熬出油,捞出油渣撒上碎盐,咸香酥脆,吃一口,香到骨子里。母亲和父亲尝也不舍得尝一口,就端给我们:“吃去吧,解解馋!”剩下来的半锅猪油,可是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调味了。
大年三十上午,父亲把各个门头打扫得干干净净,贴春联。那时候的春联不是买的,而是买来纸张,由识文断字的大伯写。大伯戴上眼镜,翻出万年历,翻飞着手中的笔墨,各式春联就挂满了院落。
下午,父亲把平时舍不得用的精美小碟子找出来刷洗干净,摆放在堂屋客厅的方桌上。然后,精心制作供品——青萝卜削鲜桃儿。萝卜顶端青的部分是桃子的底部,萝卜根部的白色部分是桃子的尖儿,再用红纸把桃尖儿染成紅色。这染色也是有讲究的,桃尖儿最红,渐远渐淡。桃子的蒂连接菠菜叶,一个鲜灵灵的桃子成了,极像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放在碟子里足以乱真。
相关阅读
-

旧故事:父辈们
台湾的十六弟书仁,清明节要回老家上坟,我去郑州飞机场接他。 十六弟是九叔父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特别像二奶奶。机场出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九叔父去台湾前是国民党洛阳
-

小说故事:牛粪也有着独特的清香
官里传出消息,皇上纳妃,当朝官员如有待嫁女儿,可以将画像上呈甄选。 李知府很激动,他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待字闺中。 当然得先找一名画师。 应征者络绎不绝,经层层筛选,入
-

生活随笔:心地善良,心怀悲悯,一生定能行好运
清晨的校园里,清风习习,鸟鸣啾啾。 一如往常,在学校操场边的一排香樟树下,我胡打了一通自创的“五禽戏”,拉伸后,准备再做一百个俯卧撑。刚趴下来没做几个,突感有东西掉
-

生活随笔:回忆,过去的甜味儿
北方人嗜酸,南方人爱甜,肉羹里都放糖。汪曾祺老先生说:“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肉包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饭菜里都放糖,虽然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