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追着我脚步的风
风 吹进铁佛庵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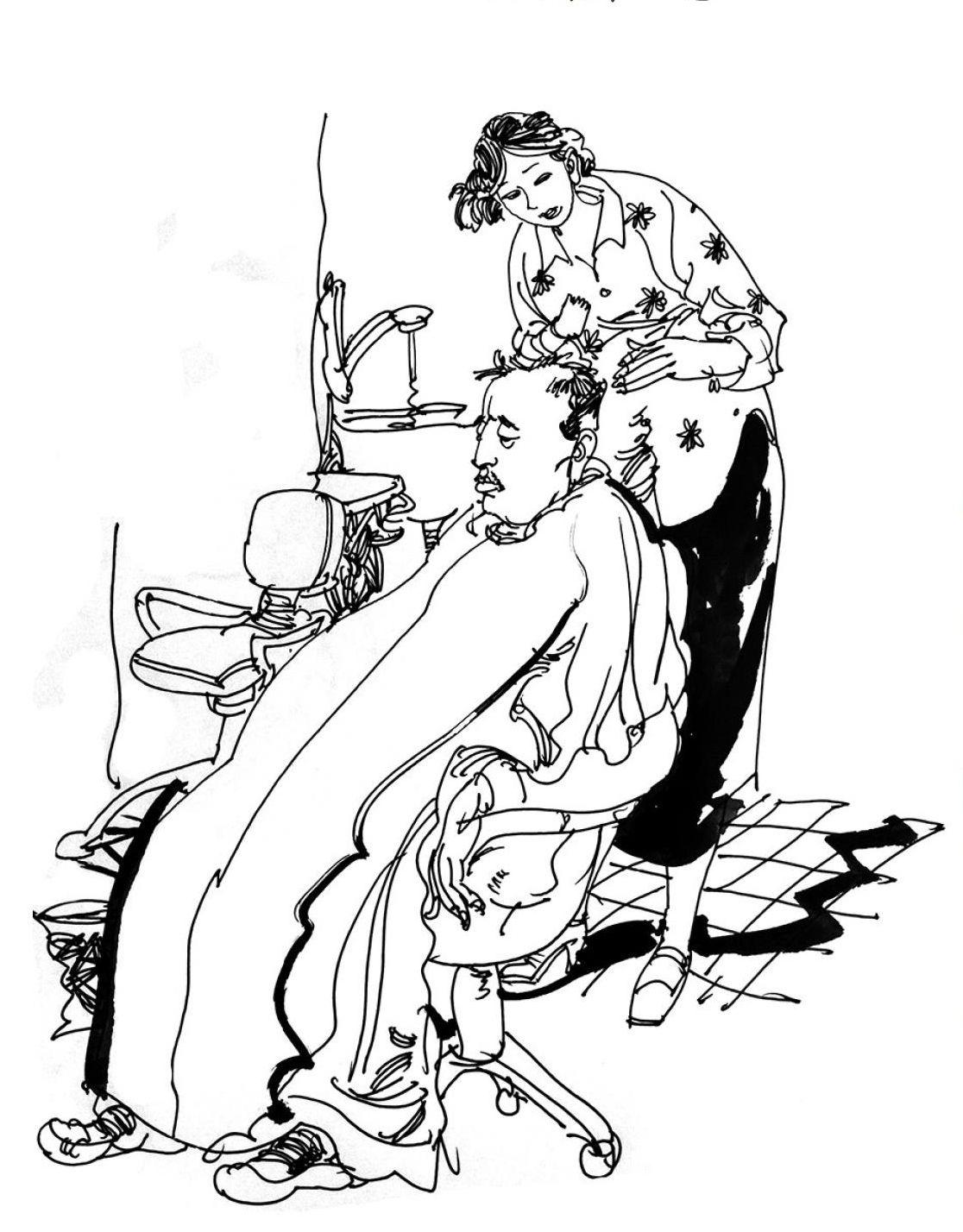
1
左弯右拐,上坡下坡。我在铁佛庵小巷慢悠悠地走着。时间也在慢悠悠地流淌,如一架老钟表,指针上沾着灰,一步一步迟钝地走着。
一口老井卧在那儿。井外围着几个硕大的磨盘,一圈高高的井栏把它们圈起来,仿佛一块大卵石,固定在岁月的河中,不动了。
风来了,风摇落了井边枇杷树上的花,细细碎碎的,纷纷扬扬地落进了井里,扰乱了井水的平静。
井说话了。它幽幽地对我说,很久以前,我是那庵中的井,因庵中供奉着一尊大铁佛,人们称其“铁佛庵”,我被称为“铁佛庵井”。我与庵中尼姑一样,过着清净的日子。一百多年前的一阵炮响,扰了我的清净,铁佛被熔化,筑成炮弹。炮弹爆破的烈焰笼罩了四野,我的身上染满了血。后来,天下太平了。我成了人世间的“市井”,迎来了我最开心的日子。每天天刚亮就有人来取水,水桶撞击声,木杵声,说笑声,不绝于耳,直到天黑还人影绰绰,那个热闹哦——
围在井边的石磨也说话了,当年,我们在磨粉厂工作时,也是忙个不停,那么多大磨子一起转起来,呼呼嗖嗖,轰轰隆隆,那个排山倒海的气势!
星子般的花瓣儿,隨着风在石磨上打着旋儿。
唉——老井与石磨一起叹息,我们退休了,那些过往,人们恐怕早已忘了。
忘了吗?井东边一排长条石凳上,三五个老人坐在那里,面朝着老井呱白,从先,人到了棺材里,棺材到了庵里,庵里老尼姑坐在青灯下为棺材里的人超度。磨粉厂磨出的白面,那个麦香,香了几条巷。近前去打听,他们十分笃定地指出了铁佛庵及磨粉厂的位置。自不消问,他们是否记得当年打水洗濯的事了。
打井水的铅桶、井边的晾绳早已在风中不知所踪,还有当年让小巷冒出炊烟的一套工具,煤球炉、芭蕉扇、火钳、一小把劈柴,也都随风星飞云散。旧事里那辆板车也耗尽一生精力,去向不明。
旧物不存,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蹲在人的记忆里,冷不丁雀跃而出。
“万物轮回,这是自然规律……”已然走远,风又把井边老人的话送过来。
2
被风送来的还有季节的口信。
碧绿的莲蓬、鲜红的菱角、白萝卜、紫茄子、青瓜,活蹦乱跳的小虾,扑棱尾巴的时鱼,团成圈绳的黄鳝,还有门上插的菖蒲、浸在水盆里的粽叶,牵着泥土,带着池沼,挽着时令节气,一起来到小巷里;黄澄澄的菜油、白花花的大米、红艳艳的花生米,在粮油店门口招徕着你;花花绿绿的绵绸悬满小小的布店,争奇斗艳地招展着;撒着黑芝麻的白糍糕刚出笼,袅袅的白气飘着诱人的甜香。好吃的多着呢,甜米酒、炒米、芝麻粉、豆腐脑,还有骑着电动车、挂着喇叭来回叫卖着的“北方大馍——老面馒头——”与高音喇叭声应和着的是穿蓝布衫的老奶奶悠悠的一声“白兰——花——”她坐在掀着一角白布的竹篮边,一股幽香钻出了布角,袅绕在小巷中。这些声色气味尽是季节的味道、色彩和诱惑,让人活色生香地生活在那天、那月、那年里。
相关阅读
-

旧故事:父辈们
台湾的十六弟书仁,清明节要回老家上坟,我去郑州飞机场接他。 十六弟是九叔父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特别像二奶奶。机场出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九叔父去台湾前是国民党洛阳
-

生活随笔:回忆,过去的甜味儿
北方人嗜酸,南方人爱甜,肉羹里都放糖。汪曾祺老先生说:“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肉包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饭菜里都放糖,虽然味
-

小说故事:牛粪也有着独特的清香
官里传出消息,皇上纳妃,当朝官员如有待嫁女儿,可以将画像上呈甄选。 李知府很激动,他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待字闺中。 当然得先找一名画师。 应征者络绎不绝,经层层筛选,入
-

生活随笔:心地善良,心怀悲悯,一生定能行好运
清晨的校园里,清风习习,鸟鸣啾啾。 一如往常,在学校操场边的一排香樟树下,我胡打了一通自创的“五禽戏”,拉伸后,准备再做一百个俯卧撑。刚趴下来没做几个,突感有东西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