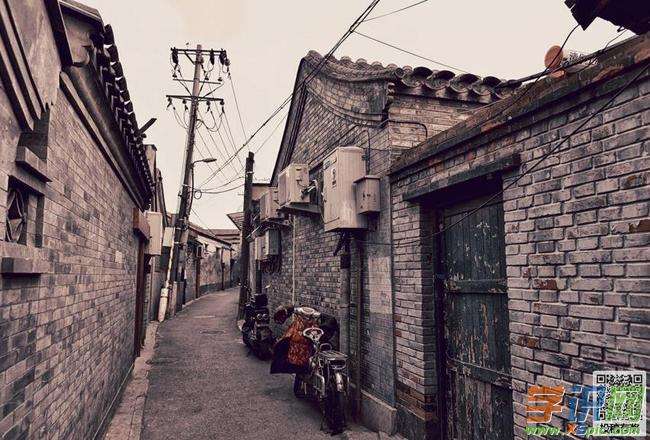生活随笔:里下河,承载了艺人们太多的想象与乡愁(4)
嗨呀嗨哟嗨幺
采访结束后,他笑了。笑容里只闪现出一丝丝腼腆,抑或是谦逊,便再无推辞忸怩。他回到演出队中,一嗓子唱出:
嗨——
太阳一出热炸炸咪。
诸位先生!
浑身汗水如雨下来。
嗨幺!嗨幺!
嗨呀嗨哟嗨幺!
嗨呀嗨哟嗨幺!
大田等水插秧苗,先生!
我们晓得咯!
……
里下河水乡立时活起来、动起来,让人恍惚进入一个新时空。那声音悠扬高亢,奔放开阔,荡气回肠,与歌手一样,是不加修饰的健康之美。周边的响动悄然静止,所有人都专注在无边的曼妙里。
我从未在这样的情景中听过这样的声音。因为那一刻我便认定,这劳动号子、这车水号子就是旷野的声音。
因为震撼,让我更感到里下河农民的艰辛与不易。不过,就在那一刹那,可能还是因为震撼,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
那个时候,农村没电,更没抽水机,稻田的灌溉便成了农民的一块心病,怎么办?办法总是有的,但是,灌溉的用具就太原始了,靠的是一种古老的木制农具水车。车身长长的,用作水槽,斜搁在河沿上。两头装有大小齿轮,绕着一长串序板。岸上一头的齿轮套在一根大轴的中央,轴上装有若干脚蹬,这是踏水使劲儿的部位。大轴两边有架子托住,且架子的上方搁着一根粗细适中的毛竹。就这样,踏水人扶着竹竿,踩着脚蹬,转动齿轮,带动序板,便把河里的水提到岸上,从而哗哗地流入田间。
因为那时我太小,倒觉得这活儿新鲜、潇洒,更好玩儿,但后来听爷爷讲,踏水这活儿干起来并不轻松,并非像走路那样容易。4个劳力8条腿必须步调一致,得掌握好齿轮转动的速度,不快不慢、不先不后,找准脚蹬的恰当角度,适时用力,既得劲儿又安全。踩慢了,脚蹬会转过了头,不仅使不上劲儿,反而人还要滑落下来。踩早了,脚蹬还没转过来,用反了力,加上水流向下的力,使齿轮反转,脚会被飞转的脚蹬打伤,严重的还会出血,更糟糕是,序板也会被损坏。而此时踩水的人只能将整个身子吊在竹竿上,当地百姓俗称“吊田鸡”。刚学踏水的人,吊上几次“田鸡”那是常有的事,但吊多了,会被他人冷落的。因为完不成当天灌溉的田亩数,大家的工分是要被记工员扣除的。所以,车水从清晨三四点就开始不停地踩,总是感到有走不完的路、踏不完的水,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多才能收工回家。那些人啊,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浑身像散了架似的。
多苦啊!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眼前。真的太敬佩里下河人的智慧了,在那个年代就懂得用歌声、用劳动号子在吆喝声中传递劳作信息,在唱和声中协调劳作节奏,在哼唷声中表达劳作欢愉,在咿呀声中抒发劳作向往。
相关阅读
-

小说故事:牛粪也有着独特的清香
官里传出消息,皇上纳妃,当朝官员如有待嫁女儿,可以将画像上呈甄选。 李知府很激动,他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待字闺中。 当然得先找一名画师。 应征者络绎不绝,经层层筛选,入
-

生活随笔:回忆,过去的甜味儿
北方人嗜酸,南方人爱甜,肉羹里都放糖。汪曾祺老先生说:“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肉包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饭菜里都放糖,虽然味
-

生活随笔:心地善良,心怀悲悯,一生定能行好运
清晨的校园里,清风习习,鸟鸣啾啾。 一如往常,在学校操场边的一排香樟树下,我胡打了一通自创的“五禽戏”,拉伸后,准备再做一百个俯卧撑。刚趴下来没做几个,突感有东西掉
-

旧故事:父辈们
台湾的十六弟书仁,清明节要回老家上坟,我去郑州飞机场接他。 十六弟是九叔父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特别像二奶奶。机场出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九叔父去台湾前是国民党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