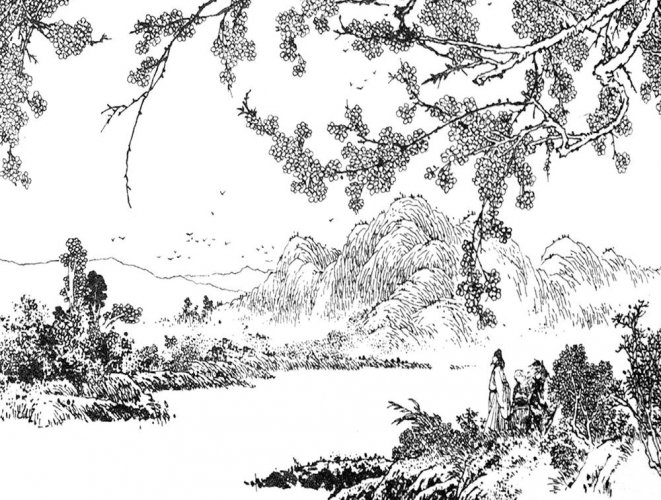生活记忆:妈妈的手擀面(2)
面条
细面条就比较讲究了。和好的面团要醒一会儿,让面充分发酵;面皮要擀得尽可能薄,甚至有些巧媳妇能擀成蝉翼状;切面条时要精打细算,严控刀口,这样出来的面条就真真如黄庭坚诗中描述的“银线”般了。细面条更适合蒸。面条擀好之后,在篦子上平摊均匀,置于锅上慢蒸。之后将蒸好的面条倒入早就备好的菜锅中(多用长豆角),混在一起,再用小火焖上一焖,故老家也称之为“焖面”。出锅之前,浇蒜汁拌匀,蒜香、面香、蔬菜香就会扑鼻而来,令人垂涎三尺,欲罢不能。焖面都是干货,很是顶饿。农忙之际,焖上一锅,美餐一顿,最出力气。工作后,我常于施工单位流连,工地中农民工最喜焖面,便宜顶饿不说,偶尔还可奢侈一回,来瓶啤酒,不仅解乏更解思乡之情。
除了粗细,面条还有宽窄之分,著名的河南烩面或安徽板面就是以宽面条为原料。同样著名的山西刀削面在形状上就会随意许多,甚至要看师傅的刀工或心情。但无论哪一种面,都是远在他乡之人魂牵梦绕的滋味。
三
面条的辅料亦多种多样。
黄瓜,亦菜亦瓜,为世人喜闻乐见,也是面条的最佳拍档之一,甚至对于凉面,少了黄瓜就无法成席了。黄瓜切成丝,面煮熟过凉水,将两者置于碗中,浇上蒜汁,搅拌均匀。由于浇了蒜汁,我老家又称之为“蒜面条”,清爽可口,尤适合于炎炎夏日食用。犹记得,夏日中午,众乡亲纷纷端碗而出,来到村中小庙屋处,各自找墙根儿蹲下,相互一看,多为“蒜面条”,然后就边闲聊边“呼噜、呼噜”地吃面,声音此起彼伏,宛若乐队演奏。吃面条若不发出声响,大抵如男欢女爱之时没有任何喘息一般,实在大煞风景。但这种特有的“呼噜”之响,有时也会演变成家庭战争的导火索,这可能是吃面唯一的副作用了。
北京的炸酱面也是要加黄瓜丝的,但它不用蒜汁,而是用酱,并且也不止加黄瓜丝,还有胡萝卜丝、豆芽菜等,据说将近二十种之多,其程序之烦琐,做工之考究,用料之精细,绝对配得上“北京”二字。遗憾的是,我来北京已有十三年之久,对炸酱面始终提不起兴致。大抵是泥腿子出身,对带着皇家范儿的食物有种天生的敬畏。我突然想起刚来北京第一次坐公交车的样子,灰头土臉又怯生生的,怪不得售票员总拿眼斜我,现在想起还依然浑身不自在。看来我还是老老实实吃自己的蒜面条为妙。
不同于我们老家爱吃蒜面,北京这边常吃的是打卤面,而西红柿鸡蛋卤应是最常见的。面煮熟后捞出,可过凉水,也可不过,然后置于碗中,上面浇上西红柿鸡蛋卤,西红柿的酸味儿搭上鸡蛋与面条的香味儿,色香味俱全,沁人心脾,令人食欲大开。可能生于北京,我儿子和姑娘对西红柿打卤面就情有独钟。他们往往将卤放满,拌匀后再吃。这在我看来已经与汤面无异,但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而且是连汤带面一起下肚,奇怪的是他们对汤面却没有这么大的兴致,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西红柿打卤面可大俗也可大雅,大俗时普罗大众人见人爱,大雅时可登堂入室成为达官贵人的“座上宾”。人世种种,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其实都不过是图一肚饱耳。
相关阅读
-

小说故事:牛粪也有着独特的清香
官里传出消息,皇上纳妃,当朝官员如有待嫁女儿,可以将画像上呈甄选。 李知府很激动,他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待字闺中。 当然得先找一名画师。 应征者络绎不绝,经层层筛选,入
-

生活随笔:回忆,过去的甜味儿
北方人嗜酸,南方人爱甜,肉羹里都放糖。汪曾祺老先生说:“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肉包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饭菜里都放糖,虽然味
-

旧故事:父辈们
台湾的十六弟书仁,清明节要回老家上坟,我去郑州飞机场接他。 十六弟是九叔父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特别像二奶奶。机场出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九叔父去台湾前是国民党洛阳
-

生活随笔:心地善良,心怀悲悯,一生定能行好运
清晨的校园里,清风习习,鸟鸣啾啾。 一如往常,在学校操场边的一排香樟树下,我胡打了一通自创的“五禽戏”,拉伸后,准备再做一百个俯卧撑。刚趴下来没做几个,突感有东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