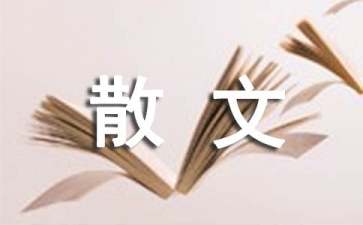历史笔记:人生需要信念(4)
梦回先遣连
吴德寿说他保全了生命算是幸运的,有多少边防战士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昆仑高原,有的连遗体都找不完整。1982年5月5日,战友谭小明奉命带队执行赴西藏阿里的运输任务,10日,车队行至海拔5470米的界山达坂时,突遇罕见特大暴风雪,气温急剧下降,路面积雪越积越厚,低洼处达两米多深,昆仑山顿时成了风吼雪舞的世界,一米开外看不清道路。谭小明驾车在前开道,高寒缺氧,他和战友都出现头痛、呕吐、呼吸困难等高山反应,但他顾不上喘口气,继续迎着暴风雪探道前进,连续奋战55个小时,终于为车队打通了前进的道路。由于过度劳累和风寒袭击,他患了感冒,引发了严重的高原肺水肿,生死关头,他全然不顾自己,带领战友先后救出了6台兵车,使陷入绝境的战友和藏族群脱离了险境,而他自己却在5月14日永远停止了呼吸。在昆仑高原的康西瓦烈士陵园,埋着数百名守防官兵。在我的心中,这些长眠在昆仑高原的战友早已化作了西部边关的巍巍山脉,成为永恒的时代楷模。
我在边防工作13年,先后6次赴喀喇昆仑和阿里高原守防施工,遭遇到的苦难虽不及吴老兵,但高原的经历也足以使我铭刻终生。刚上高原时,因体质瘦弱,到了海拔5200多米的哨卡,我就头痛欲裂,用背包带扎紧脑壳仍痛得呕吐,加之长期吃脱水干粮和压缩饼干,不到110斤的身子瘦成80余斤。有一次患了感冒,曾两度昏迷,军医徐东亮日夜守护在我身旁给我服药喂水,也许命不该绝,我居然奇迹般的活过来了。1983年3月,我奉命随师架设分队前往昆仑腹地甜水海至哈巴克路段担负架设通信线路任务,打桩架线、搬运电杆,都是强体力活,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寒区,一天劳动下来,我们躺到帐篷里四肢无力、头昏脑涨,天天都似生了重病一般。这时,我已提干,我便学着先遣连老前辈的做法,忍着劳累和病痛,不停地给同志们讲先遣连进军阿里战天斗地踏昆仑的事迹,鼓励大家一定要像先辈那样攻坚克难,挺起脊梁,坚决完成组织交给的艰巨任务。这一招真管用,大家鼓起精神,相互激励,顺利完成高原通信线路架设任务,改写了高原无电话的历史,接通了昆仑山与全军联通的电波,受到军区的表彰。在昆仑山,我和战友曾奉命外出执行任务时与野狼搏斗过;我乘的车在途经黑卡达坂时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掩埋过;身体最瘦时仅40公斤,曾经头上、脸上、背上、屁股上长出莫名的小疖肿,有的还渗出黏黏的脓水,连续几个月每晚睡不足两个小时。在这种境况下,我始终用先遣连前辈的精神激励自己:决不能临阵倒下,一定要给先遣连增添荣誉。我和我的战友们做到了“宁可透支生命,不让使命欠账;虽然有愧亲情,不叫责任缺失”。我们是先遣连的兵,是顶天立地的军中铁汉。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回忆,过去的甜味儿
北方人嗜酸,南方人爱甜,肉羹里都放糖。汪曾祺老先生说:“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肉包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饭菜里都放糖,虽然味
-

旧故事:父辈们
台湾的十六弟书仁,清明节要回老家上坟,我去郑州飞机场接他。 十六弟是九叔父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特别像二奶奶。机场出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九叔父去台湾前是国民党洛阳
-

小说故事:牛粪也有着独特的清香
官里传出消息,皇上纳妃,当朝官员如有待嫁女儿,可以将画像上呈甄选。 李知府很激动,他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待字闺中。 当然得先找一名画师。 应征者络绎不绝,经层层筛选,入
-

生活随笔:心地善良,心怀悲悯,一生定能行好运
清晨的校园里,清风习习,鸟鸣啾啾。 一如往常,在学校操场边的一排香樟树下,我胡打了一通自创的“五禽戏”,拉伸后,准备再做一百个俯卧撑。刚趴下来没做几个,突感有东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