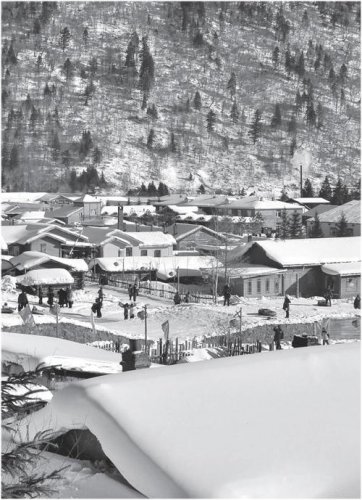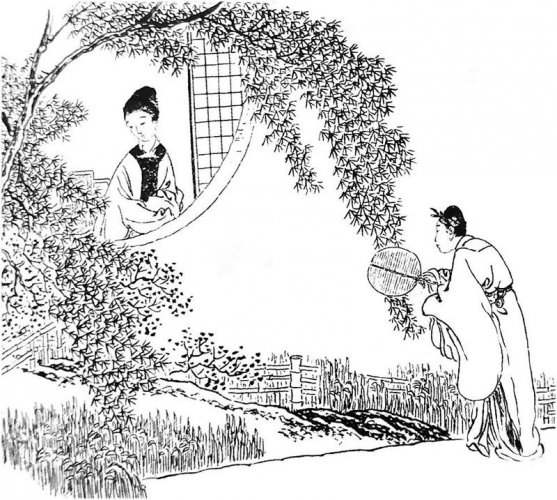生活随笔:我早已故去的父亲(4)
蓝衣
“是长相?”我问。
“不止这样,还有说话那姿态,嘴角上扬的样子。”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叔叔补充。这个人从县城的铁厂退休,是个老工人,但他老家和我父亲的外婆家不远,所以他们很早就认识了。
“你父亲只编簸箕不收边沿,”石叔接过话头说,“很多主意是他出的,但总做不到最后。”
这样的话在几天后去拜访比父亲小七八岁,一起在上世纪80年代初做生意的刘叔的时候,他说了同样的话。刘叔和石叔一样,是县城里专门有自己做生意待客酒店的人。他们的酒店都在一条街上,就是县城的正街。刘叔的更豪华,但那是之后才建的,最早是石叔。我并不能打通刘叔的电话,还是石叔帮的忙。
看到刘叔的时候,他张着双红色的眼睛向我走过来,一起走过来的还有两个人。我是从走过来的三个人的姿态里判断出谁是他的,他那养尊处优的气质,还有那霸气或戾气,都是县城里的一般人所没有的。后来,红眼睛刘叔领我到他宽敞的里外不知几间的办公室,与我单独会面。
他似乎刚喝了很多酒,脸红得如同才从桑拿房出来。他给我的感觉是亲和的,但他说话并没有那么亲和,许是因为正接受所谓“上面来的”检查。他可能真的那几天特别忙,也可能急于送走我,所以表现得特别忙,只给了我十多分钟交谈的时间。他说我和我父亲简直一个模子。从小到大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话,但都是从村子和亲戚那儿听到的。我觉得他们说的像应该是相貌上相像。而被石叔和刘叔以及其他和父亲打过交道的人说出,恍然间,我知道他们另有所指。也许是我说话的语调,也或者是我的那种肆无忌惮。我想到曾经在一次活动中遇到一个喜欢算命的人,他热衷于知道我的生辰八字,但我根本不打算告诉他。父母在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算命,他们连出门的云彩都要看的,风吹哪个方向都要占卜。他们喜欢数字,但只用于占卜而不用于规划,尤其在钱方面,结果我们家的生活一直很潦倒。不过,感谢从小的耳闻目睹,使我后来自学《易经》毫无阻隔,两次大考都因为这道题拉开了与其他没有这方面功底的同学的距离,我应该是先天基因里就有巫术的根底。然而,于具体的生活中,我不喜欢有人来占卜我的命运,我习惯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父亲那样的死亡我都经历过来了,人生自不必太多挂碍和谋划,日子就像敲钟,此刻敲响了就是敲响了。那个人还是遏制不住自己的算命冲动,说我姓名里“欣”虽为生发,但拆开来缺斤短两。几乎像一种宿命,我被他说的那短短的词句震住了。在那之前的生命历程确实是,每逢大考,我总只差那么几分。在那之后的一次大考,亦然。我已经很小心。从父亲这里就如此了。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尽量去周详地做每件事,尽量让事情看起来有头有尾,因为在从小到大的无数告诫里,都是:“你父亲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从来做不完一件事。”这些事包括他做的各种生意,也包括他第一次订婚的女人,还有很多他们欲言又止不为我们所知道的事,几乎每个认识父亲的人都会在我们做某件事半途而废时说:“和他父亲一个样。”也许,父亲一辈子能算完成的一件事就是娶妻生子。虽然我们被他甩给祖母,由着祖母和叔叔带大,但看起来至少形式上是种完成。我们生怕基因里的那种有始无终追着,我指我和姐姐,不知道哥哥是不是,反正我知道我们俩。很多时候,甚至大多时候,不管是事情还是感情,或是说爱情,我总虎头蛇尾,新鲜感很快就用尽了,一点儿都没有了,缺斤短两的宿命结尾就摆在那里了,就如经常开头却没有结尾的文章。
相关阅读
-

生活随笔:回忆,过去的甜味儿
北方人嗜酸,南方人爱甜,肉羹里都放糖。汪曾祺老先生说:“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肉包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饭菜里都放糖,虽然味
-

小说故事:牛粪也有着独特的清香
官里传出消息,皇上纳妃,当朝官员如有待嫁女儿,可以将画像上呈甄选。 李知府很激动,他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待字闺中。 当然得先找一名画师。 应征者络绎不绝,经层层筛选,入
-

旧故事:父辈们
台湾的十六弟书仁,清明节要回老家上坟,我去郑州飞机场接他。 十六弟是九叔父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特别像二奶奶。机场出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九叔父去台湾前是国民党洛阳
-

生活随笔:心地善良,心怀悲悯,一生定能行好运
清晨的校园里,清风习习,鸟鸣啾啾。 一如往常,在学校操场边的一排香樟树下,我胡打了一通自创的“五禽戏”,拉伸后,准备再做一百个俯卧撑。刚趴下来没做几个,突感有东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