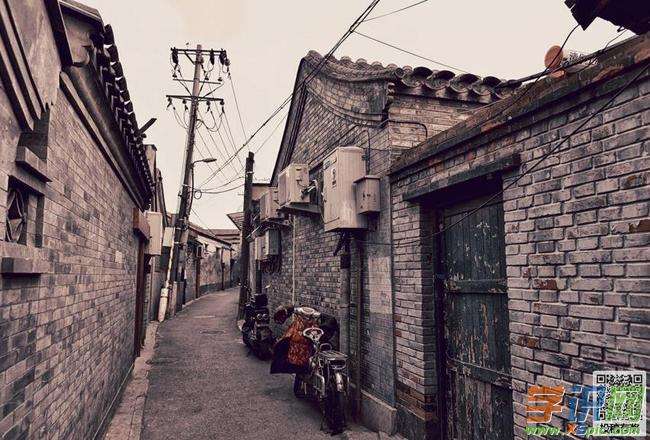散文小辑:给他们一个家(2)
陈荣娣的故事
“你还要我说呀?你自己知道的。”
小孩子能做什么呢?不外乎就是扫扫地,喂鸡、喂鸭、喂猪,还有就是看好这个家,有时跑跑腿儿而已。
老太婆看着这三个听话的孩子,是自己把他们一口一口地喂大,这么艰苦的路都走过来了,辛苦即将过去,此时,她心里甜甜的,觉得很安慰,这一刻她把所有的辛苦都忘掉了,只觉得心里好踏实。这一天又这样开始了。
50岁的陈元娣和丈夫离了婚
1935年,陈元娣出生在惠东县沿海一个渔民家庭,全家的生活靠父亲出海打鱼为生。陈元娣家在岸上没有一间房子,只有一只破船,一张破网,被人称为“蛋家”。虽然陈元娣的父亲风里来,雨里去,但命运完全掌握在老天爷手上。天气好,就能打到鱼,有了鱼,便可以拿去岸上换点儿米什么的。天气不好,刮风下雨,随时都有被葬身大海的可能。陈元娣的父亲,劳碌奔波一辈子,终年在大海中挣扎,就想让家人有一餐饱饭不至于挨饿。但是,父亲始终改变不了这种命运。他生下了八个子女,以为多个人多个帮手,生活就会好起来。但是他想错了,在那个社会,自己都难于养活自己,子女多就让这个家雪上加霜了。陈元娣家里总是有了上顿没下顿,米缸从未有过隔夜粮。兄弟姐妹个个饿得前胸贴着后脊梁,几年间,他们兄弟姐妹被卖的被卖、饿死的饿死,最后只有陈元娣幸存活下来。她9岁那年,父亲几天打不到鱼,父母亲再也不忍心看到女儿被活活饿死,最后说出了那句让她一生也忘不了的话。
父亲说:“阿娣,你想不想吃饭?”
元娣点了点头。父亲含着眼泪,声音哽咽着:
“阿爸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可以让你有饭吃。”
她跟着父亲,来到了多祝的黄锦滩。父亲忍痛把她卖到增光黄锦滩一户农民家里做童养媳。
后来她才知道,卖她不久,父亲就饿死了。父亲死后,母亲也改嫁了。母亲改嫁后,又生了一个男孩儿。不久,母亲也病死了。
至此,一个好好的家就这样消失了。她在世上就再也没有亲人了,也就是没了外家人。陈元娣的心,比黄连还要苦。
我看着陈元娣声音哽咽,泪流满面,我的眼眶也湿了,一个大家庭,由于没饭吃,就散了,从此骨肉分离,永远也见不到了。
陈元娣从海边来到多祝,当了这家人的童养媳。童养媳是旧社会穷人家一种最无奈的婚姻,然而又是双方父母你肯我愿的交易。卖女的是因为养不起又想丢下这个负担,比让她死去好多了,对买方来说,其实是买个廉价的小劳动力,待她长大后不用聘礼即可以完婚,完成传宗接代的重任,也是合算。陈元娣小小年纪,在这个新家里什么活儿都要干,挑水、洗衣、割草、喂猪等,她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是,老天让她得到了一种精神,她那刻苦耐劳的精神就是那时候形成的。
相关阅读
-

小说故事:牛粪也有着独特的清香
官里传出消息,皇上纳妃,当朝官员如有待嫁女儿,可以将画像上呈甄选。 李知府很激动,他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待字闺中。 当然得先找一名画师。 应征者络绎不绝,经层层筛选,入
-

旧故事:父辈们
台湾的十六弟书仁,清明节要回老家上坟,我去郑州飞机场接他。 十六弟是九叔父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特别像二奶奶。机场出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九叔父去台湾前是国民党洛阳
-

生活随笔:心地善良,心怀悲悯,一生定能行好运
清晨的校园里,清风习习,鸟鸣啾啾。 一如往常,在学校操场边的一排香樟树下,我胡打了一通自创的“五禽戏”,拉伸后,准备再做一百个俯卧撑。刚趴下来没做几个,突感有东西掉
-

生活随笔:回忆,过去的甜味儿
北方人嗜酸,南方人爱甜,肉羹里都放糖。汪曾祺老先生说:“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肉包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饭菜里都放糖,虽然味